“And that sweet city with her dreaming spires,
She needs not June for beauty’s heightening.”
——Matthew Arnold, Thyrsis (1865)
“The city of dreaming spires”,梦的塔尖之城——距离马修·阿诺德在诗中第一次用这几个词语描述牛津城,已过去了一百六十年。一百六十年间,又有无数笔耕者学着他的样子写下这几个字,一次又一次给这座城市镶上理想的金边。今时今日,万千学子所向往的群群簇簇的梦的塔尖,我终于能说,我也攀过了。

莫德林塔(Magdalen Tower),牛津最高的建筑
现在虽这么说了,但我的牛津之旅开启的时候却没有丝毫梦幻的成分。抵达的第一日,我被三件沉重的行李困在了距离下车的客运站不足百米远的、崎岖的石板路上。超过八十公斤的行李和突然飘起的雨把我坠得寸步难行。绝望之下,我拨打了谷歌上搜来的学院的电话,请求他们派人来营救一个筋疲力尽的异乡人。我的牛津生活是这样开始的。
来接我的人竟是从录取到报道阶段一直远程与我邮件通讯的visiting administrator。比我矮一个头的她陪着我把行李拉过坑洼不平的石板路,拉进学院的门槛,扛上三楼,扛进我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的家。我的牛津生活又是这样开始的。
回想到第一天力竭地坐在房间地板上的凄惨光景,似乎是时候正正经经地说出这段话:
我于2024到2025学年赴英国牛津大学访学,隶属于摄政公园学院(Regent’s Park College)。这一年中,我的学术在案牍间飞速地成长,我的精神在砖瓦和尖塔中横冲直撞地充盈,我的同情和爱给了许多仅有一面之缘的,以及一些有幸接续此缘、留存于我生命之河中的人和事物,在傍晚的风里随着古城的钟鸣高歌。
从零起步的人文关怀
牛津是一所天才的集中营,令人无时无刻不感到“卑微”。初来乍到时,我对于如何写出一篇像样的“牛津论文”一无所知;我甚至觉得自己欠缺开始在这里学习的基础——我没有上过英语文学预科、没有接受过导师辅导制训练(tutorial)(同学院的许多美国交换生在前往牛津前已经在本校接受了相当长时间的模拟tutorial,从而帮助自己更快地适应牛津的教学模式)、更别说进行认真的学术探索了。当我焦头烂额于文学史和基础理论知识时,身边的新生同学已经能够提出细致且成熟的学术论点。每次tutorial之前我都得紧张兮兮地准备一个小时,生怕难以应对导师“苏格拉底式的”连环发问。每两周三篇论文的高强度工作量让我的日程变成了单调的“读论文-写论文”循环:花费大量时间在海量阅读材料中寻找一个可以打磨的论点,结果不知不觉间时间过了两天半,眼看着再不开始写就更没时间成文了,只好磕磕绊绊地开始发展一个自认为残次的论点,一边不甘地想着“再多看几篇文章可能能想出更好的”……就这样,我在数周的时间中摸爬滚打,一开始只会刻板地按照“摘要、介绍、主体部分、结语”的格式拼拼凑凑,后来终于在第一学期过半时学会了一篇standard Oxford essay的写法,摸清了在牛津存活的门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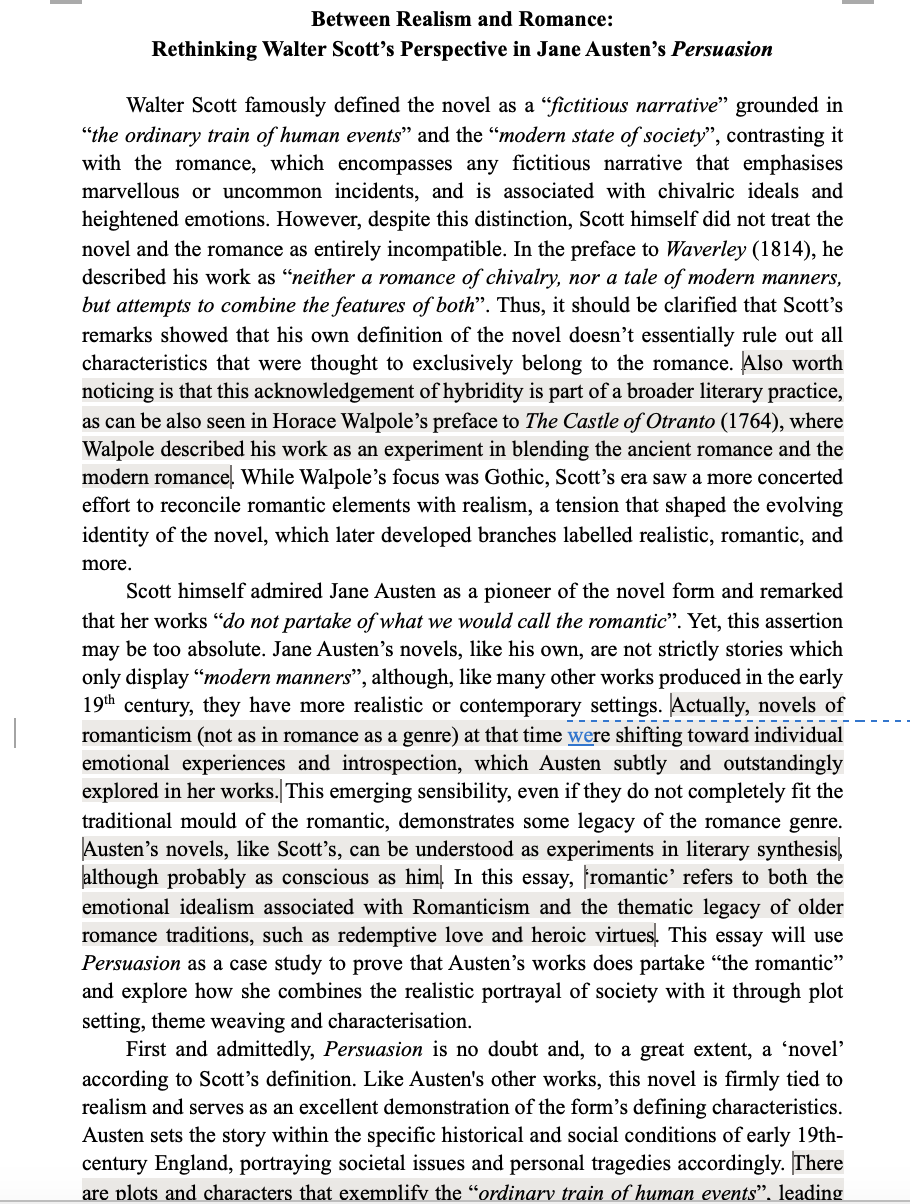
第一学期后期写出的(终于)被导师表扬的论文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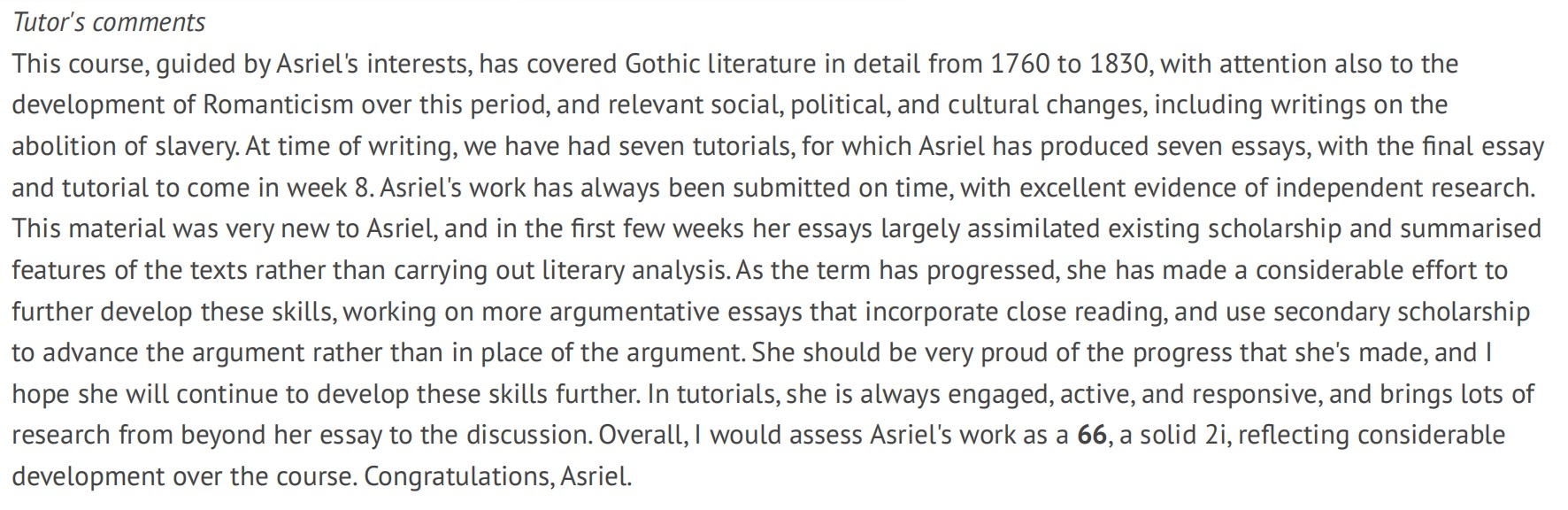
导师Helen在学期末的评语中肯定了我向牛津标准靠拢的海量努力
随后的两个学期,我不断地深入探索自己的学术兴趣。第一学期我的课程集中于英国文学研究(浪漫主义哥特文学以及J.R.R.托尔金研究)。到了第二、第三学期,我又分别学习了前现代中国白话小说批判性翻译研究(critical translation studies on pre-modern Chinese vernacular texts)、文学人类学(literary anthropology on late imperial China)、以及跨国别研究与东亚文学(transnationalism in East Asian literature),将视野拓展到了比较性质更强的文化研究上。我有幸在第三学期师从许明德教授(Prof. Ming Tak Ted Hui)学习文学人类学,在几乎完全陌生的领域中完成了八周的专题论文写作——与经验丰富、涉猎广泛的学界大能一对一交流,我没有一次不感到自己当下视野的短浅和能力的卑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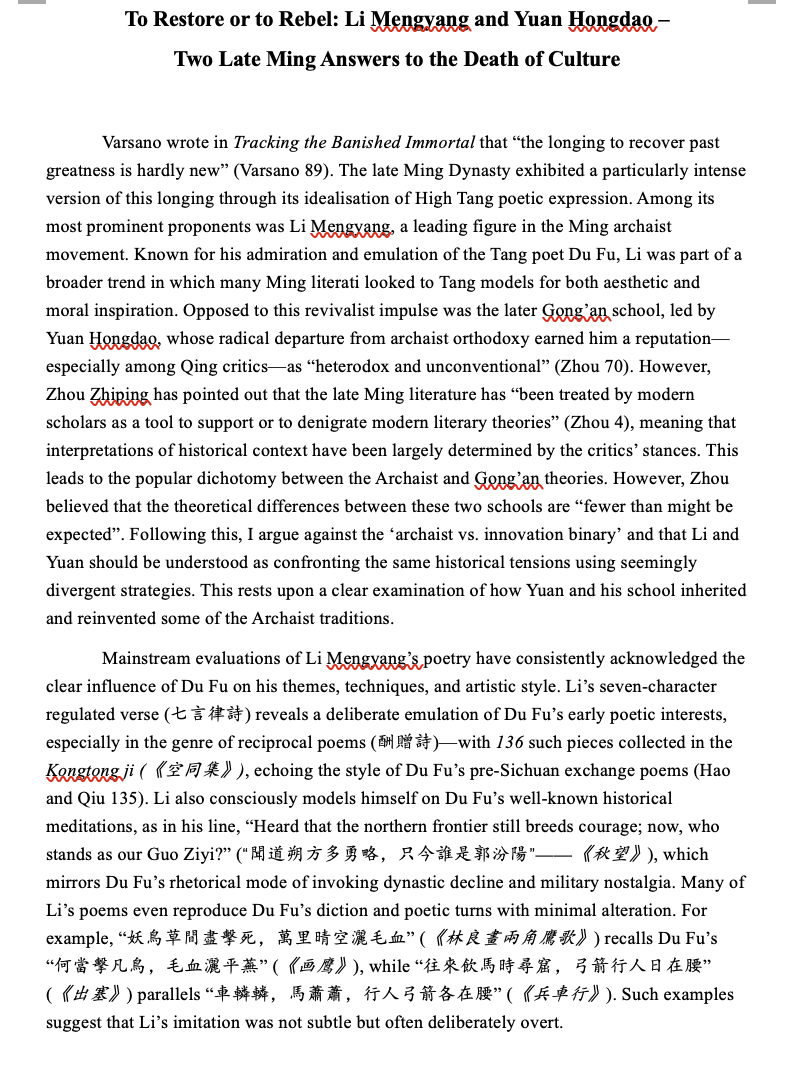
第三学期我在Prof. Hui的课上产出的论文节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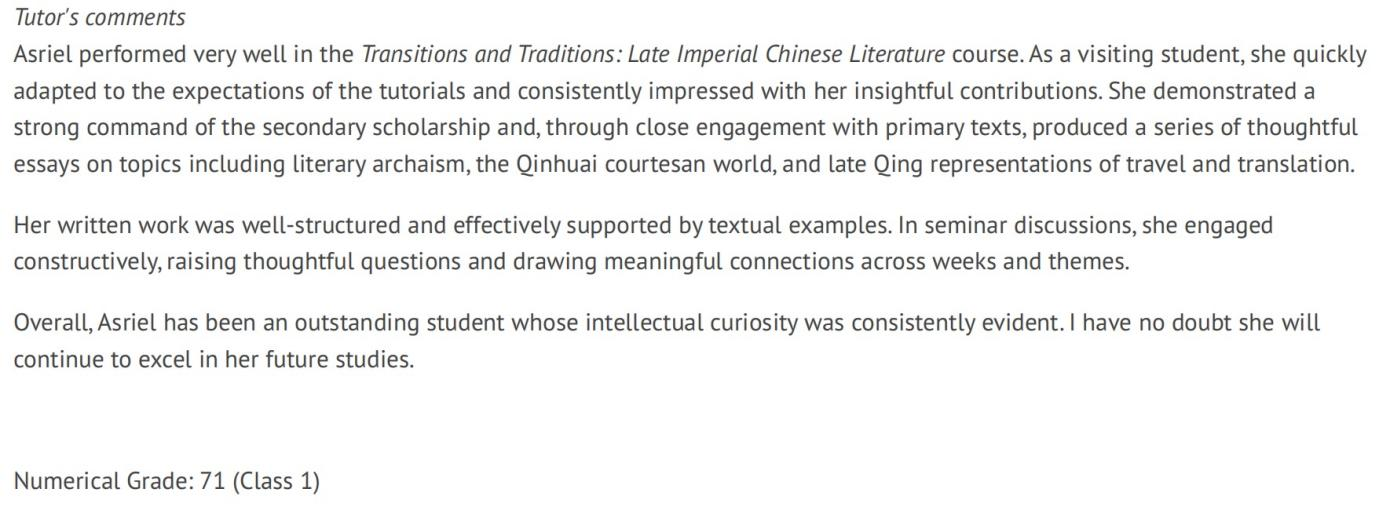
教授在学期末的评语中对我的表现给予肯定
我在一开始的研究中不断地思考和质疑人文学科的最终目的,因看不到许多学术探究对现实世界的指导或启发作用(它们大多上升至了认知论的角度)而疑惑这样的研究究竟有什么意义。然而,和Ted的一次对话让我第一次似乎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人文学科的目标迥异于自然科学的“发现客观规律”,而更注重于拓展我们理解世界和人的方式。当我们研究历史、文学、哲学——哪怕最终得出的结论无法直接改变国家政策、科学技术或经济结构,它仍然通过丰富我们对“人之为人”的想象和体认,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为了课业读到的众多文化研究的文章,其所揭示的都并非某种“能立刻拿来用”的社会逻辑,而是一种理解复杂性、同情异质性的能力。这种能力本身就是民主社会、跨文化共处、伦理判断等一切“现实问题”的根基。Ted对我说,要做一个心怀同情(sympathy)的人文学者;不带同情心地研究历史和文本,只会陷入暴力的抽象——把人看作概念,把苦难看作例证,把文学变成数据。真正的理解来自一种贴近人的经验与面对困境的耐心与敬意。最初我们被批判精神吸引,把它视作一种拆解机制、质疑权威的武器;但随着路越走越远,我们又会意识到不加节制的批判容易沦为虚无。真正重要的,是批判之后重建意义的能力——不再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更谦卑地与过去、与人性本身对话。因此,我在此向诸位人文的同窗们分享我在牛津学到的最宝贵的一份知识:人文精神不在彼岸,而在回返。我们不需要把人文学科的意义强行外推到别的学科领域去随波逐流地追求“融合创新”,而应当接受它内在的悖论:它永远无法提供唯一正确的答案,却能带来最深刻的问题意识;它的实用性常常不可量化,但却最能改变人心;它研究的往往是过去的、虚构的、抽象的,但启发的却是我们当下最真实的伦理抉择与情感经验。做一个人,持一把温柔的笔刷,即使不能抚平,也用尽心力感受并教人感受脆弱与希望。
图书馆之后:从高桌到吧台
牛津四十三所学院各不相同:历史上、文化上、占地面积上、学术专长上……最老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和莫顿学院(Merton College)建立于13世纪,而最年轻的学院鲁本学院(Reuben College)则在2019年刚刚建立;我所在的摄政公园学院(Regent’s Park College)是牛津占地面积最小的学院之一,整个学院只有一个quad(一种四方规制的院子),而占地面积最大的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光是鹿园就有数个摄政公园大。

摄政公园学院的院宠小乌龟Truffle和莫德林学院鹿园里的鹿
大学的文化为其成员所特有,和城镇自身的文化相独立。四十三所学院各自有独特的内部文化,又和其他学院同享大学的文化:每周数次的晚宴(formal dinner)——一种人人正装出席、三道菜肴、开餐前伴随着唱诗和拉丁祷告词的正式晚餐;清晨五点开始训练的划船队(众学院有自己的队伍,除此之外还有水平最高的校队,每年和剑桥在泰晤士河的大赛全球直播);定期掉落的主题BOP(Big Open Party);晚上八点开始运营的学院酒吧(Student-run College Bar)……在牛津城街头,识别出大学的学生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们要么穿着印着学院纹章的羽绒服(一种全校统一款式,左胸绣学院纹章、右胸绣姓名缩写的黑色或深蓝色羽绒服),要么穿着正装,正装外套着牛津的学术袍(academic gown,这种袍子在不同学位之间、学生与学者之间,以及普通学生和奖学金获得者之间的规制都不一样),要是都没有穿,那么戴着耳机,背着书包低头疾走的人也基本没跑。

在不同学院吃formal

和同学一起穿着学院羽绒服的合影(中间混入了剑谍)
学院砖墙外的牛津城少了领带长裙和繁文缛节,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烟火味的世界。每一个新来的学生一开始总会被城市的各种小规矩使绊子:市中心的超市周日下午五点就关门,非连锁的日本餐厅基本周一周二都歇业……慢慢地,在牛津城生活的各种小技巧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大脑;慢慢地,我知道了最火爆的拉面店下午五点半就要去排队,知道了数学系对面的中餐馆只有中午卖盖浇饭,知道了最好吃的kebab车会每晚七点开到学院外的马路上、高街转角的黑羊咖啡馆每周一有学生折扣、植物园可以用学生卡免费参观……慢慢地,我变得和牛津城越来越同频,跟着城市的节奏行走和呼吸,在她繁忙的时候去凑一阵热闹,在她平静的时候窝在炉火旁,同样静静地读一本书。
在日常之外,牛津城在不同的特殊场合也会给人献上不同的惊喜。十一月初,南郊空地建起游乐场,在初冬的夜晚上演烟火大会。十二月中,市中心建起临时的圣诞集市,售卖糖果和特色小吃。五月一日的清晨(May Day),全市人民聚集在牛津最高的莫德林塔下,等莫德林学院唱诗班在塔顶唱圣歌,宣告春天正式开始。每一次庆典都悄无声息地绑紧了我和牛津之间的纽带,悄无声息地强化着我对这小镇的归属感。

五一的塔顶唱诗以及满街的市民
人
不过,最让人舍不得的往往不是几百年的图书馆,也不是夜空里的烟花或是周末集市的东北大煎饺,而是一起去图书馆学习、一起站在草坪上看烟花和一起逛集市的人——短短一年中,我遇到了许多人;其中有很多人注定早已见完了最后一面,也有一些人我确信着,至少希望着未来还会相见。不管哪一类,其中都有这么一些人,我应该会记很久很久。我记得第一天帮我搬行李的辅导员老师Silvia,记得第一天把我专门约出门带我喝咖啡参观图书馆的加拿大学姐Lucy,记得学院厨房里声称“所有学生里最喜欢我”的主厨Mark,记得我错过社团招新报名,苦苦哀求加试后统一给我额外安排面试的社长Qingyang,记得社团里还没毕业就拿到英伟达offer的日本前辈Masato……还记得在英国终于摆脱数个月冬日阴雨的第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好友拿着表演要背的曲谱在公园的长凳上唱了两个小时的歌。

与我的两位辅导员,Tim和Silvia在学院合影

和学姐Lucy在学院最后一天的合照

在社团排练时和同声部的好友Jiayue、社长Qingyang以及前辈Masato(从左到右)合照

社团音乐会结束后的合影

参加音乐系学生的项目,在市区的教堂里演出
摄政公园学院在每学年末都会举办一场告别仪式(Valedictory),旨在送别该学年结束后要离开牛津的学生。完成学业的学生会被叫到台上,在学院的register(一本厚厚的用来保存大家签名的大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作为学院的一份子永远被“记录在案”。我签字的时候非常紧张,手抖得厉害,在书里留下了一个歪歪扭扭、颤颤巍巍的记号。如此迅速和恍惚,我已经在牛津大学完成了一阶段的学业。回国的日期也已经敲定——下一次回到博德里安图书馆,或许要寄希望于一年多以后。

Port Meadow的落日余晖
牛津城西北处有一大片草地,名叫Port Meadow。草地上放养着马群和牛群,任人走进与自然零距离接触。泰晤士河的支流也从这片草地上流过,河边停留着成群的飞雁和野鸭,偶尔会有苍鹭和天鹅。每逢晴天的傍晚,Port Meadow就会慷慨地赠出牛津最美的夕阳,一大片毫不吝啬地抹在半边天上,然后再一点点被晚风吹散。我在离开牛津的前一晚重返这片草地,重新看了一次日落——那一刻只想也化身一匹马,一直奔跑在这方和任何普通规模的城市相比都如此渺小的、却又是全世界最广袤的天地之间。
结语

在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的大草地前留念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为我提供了访学机会,让我得以体验多元的世界顶尖教育资源,感谢老师和亲友们对我殷切的期待。现在的我踏上回程,怀揣更丰富的知识、更顶尖的能力、以及更炙热的情怀,随时准备再次出发,追逐新的梦想的塔尖。